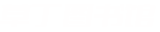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夏天的烟愁
文|三毛
电报草稿几乎发不出去。我和电信局的人在书上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找到地名。在此之前,我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驾驶地图,但是找不到小村庄的位置。
我告诉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试一试,把它送到村子附近6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上,看能不能转。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它在小镇附近。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家乡。因此,他发了一封这样的电报:“德尔Xi,邦费拉达附近的一个小镇。裂片家族收到了它。”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酒店的名字,让我的朋友Baloma和她的丈夫夏一米赶紧联系我在马德里。说起来,我们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一米是我们婚礼的见证人。对西撒哈拉的占领结束后,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多次搬回家,因为很难找到工作。当我最终搬到加那利群岛时,我的丈夫何塞已经去世七个月了。事实上,巴洛玛和夏伊米成了亲密的家庭成员,他们总是一起度过假期。当时,沙漠里的老朋友大多都快死了。他们和我都是这片土地的爱好者。相处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种乡愁和悲伤需要去理解。然而,在离开沙漠后的岁月里,似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加倍艰难。夏一米已经很多年没有连续工作了。他们的生活非常紧张。
1982年,当我从台湾省回到加那利岛的家时,邻居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Baloma病得很重,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夏一米赶紧让邻居告诉我,他们已经付不起房租了,带着两个男孩搬回了西班牙。Baloma的母亲有一些祖传的村庄可以居住。而且我们平日也不怎么交流。
在了解了Baloma之后,我早早离开了这个岛,飞往马德里。我赶到Baloma父母在郊区的花园房子,却发现它变成了土地,一套公寓正在建造中。出于找不到人的焦虑,我发了一封没有地址的电报。第二天一早,夏一米的长途电话来了。他说第二天一早去马德里接我,去乡下住几天。最初,这个叫德尔·Xi的家乡是一个梦想之地,每年Baloma的孩子们都会回到这里度过暑假。照片里见过很多次,就是没去过。这一次,我想不出在这种情况和心态下还能走下去。
中午,我站在酒店的街上,告诉认识我很多年的老门房,车一到就要帮忙放箱子。那个小旅馆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所以绝对禁止停车。当它停止时,警察会立即惩罚它。
计算行驶距离。如果夏一米早上6点从家乡出发,他可以在中午1点左右到达马德里。我住在老地方,我的朋友都知道。下午1点半站着,夏一米的胖胖身影出现了,我赶紧跑过去拎行李,匆忙往后备箱里塞东西,抱住了老门房,跳进了车里。我以为他是唯一来见我的人。当我进入前排座椅时,我意识到Baloma半躺在后备箱里。那辆老爷车大,我赶紧从前座爬过手挡的空缝隙,推到前面。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Baloma被裹在毯子里,被一个大枕头覆盖着。我走上前去亲吻她的脸颊,抬起她的双手,放在我的脸上,温柔地问:“亲爱的,你能看清楚我吗?”说话的时候眼睛湿了,声音却很安静。她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没有梳短发,就像一根枯黄的麦秆。想起我们在沙漠里用旧布缝在一起的情景,我的心里充满了沧桑。
带我出城,快点,周围太吵了。巴洛马说。我在一个不太拥挤的街角下了车,买了一大包饮料、奶酪、火腿和面包,然后又上车了。夏一米说要一路开车去农村,七八个小时后晚上十点就能到家。Baloma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瘦削的脸让她老了很多。吃了一口三明治,他说没胃口,叫我吃。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
推荐阅读
- 好的爱情是天堂,坏的爱情是地狱
- 90后结婚后,比婚前更孤独
- 子夜荐读 | 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 三毛流浪记主演 《三毛流浪记》的扮演者已长大 曾因头部受伤息影7年 至今单身
- 子夜荐读 | 纠结无用,不如让心思简单些
- 子夜荐读 |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 子夜荐读 | 有一种自律,叫熟不逾矩
- 子夜荐读 | 人到中年,要学会给自己看“病”
- 子夜荐读 | 人生如镜,镜透百态
- 武汉市漫画研究会新任掌门人蒋勇呼吁:“三毛式的传统漫画急需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