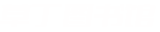说到村子,Baloma就多说了一点。我说,寡妇们怎么了?巴洛玛哈哈哈大笑,然后突然指着我身上一条有花丝的西班牙披肩说:“如果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他们会马上骂你。不要把你的事告诉他们,也不要理睬他们——”
她不知不觉,我和夏一米吓得跳了起来——巴洛玛什么时候看到我的颜色了?!她一点也不瞎。她不是瞎了就是没瞎。视神经绝对没有问题,是巨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夏一米失业两年多把她带了出来。
“你看到我了吗?看到了吗?”我试图捏住巴洛玛的肩膀,尽可能用力摇晃她。“啊,啊——”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歇斯底里地推了我一把,然后摔倒了,不再说话。
“爸爸妈妈?”我再次躺下,对夏一米耳语。“爸爸在马德里市中心做手术,不要告诉她。”当然,我知道Baloma的整个家庭。她的母亲是一个可爱迷人的女人。Baloma没有她妈妈好,她也不会每天把自己打扮得一团糟,但是她的家还是很漂亮。她喜欢打扮她的家人和做蛋糕。我的结婚蛋糕是Baloma做的。因为太敏感了,所以不会出来做职业女性,人也很傲慢。如果他们一句话不说,长得好看,就会把心交给别人。
天渐渐黑了,袁野身上的星星空就这样亮了起来,一颗颗挂在窗外。茫茫荒芜的黑夜和天空空引起了我心中熟悉的痛苦。十七年来,我疯狂地爱着西班牙这片土地,一刻也不厌倦。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化。在加斯蒂亚之后,夏天的热度消退了,初秋的凉意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
Baloma好像在睡觉。夏一米让我做第七个厚三明治。他已经很胖了,个子不高,96公斤,还吃得很辛苦。那种吃相让人觉得他是个不顾一切的家伙,是个很不开心的胖子。把吃饭作为生活匮乏的唯一慰藉。
经过电报上写着“Bang Ferrada”的小镇后,我看到火车站旁堆着的景山公园,相当封闭,风平浪静,覆盖了整个城市,没有任何活动。
民风保守沉闷,这是我的印象。夏一米每天开车来这里找另一份工作,但事情不能太多。这个城市的经济可能比发展更成功,一眼就能猜到。这个城市的餐馆不多,这意味着人们花的钱不多。就是药店,看了好几本。
穿过城市,我们变成了一条柏油路,这条路很小,两旁是大片的松林。汽车开始爬山,山下小镇的灯光也在暗暗的微弱。在山里,东边有一盏灯,西边有一盏灯,这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在晚上感到孤独和宁静。但是,毕竟有太多的孤独。
开了40多分钟,我来到一座小桥前。当汽车转向左边时,沥青路面结束了。真正的泥路和大石头惊醒了没说话的Baloma。她坐起来,靠在我身上,用手摸索着,摸着她的羊毛披肩。她摸了摸。“教堂在这里。”巴洛马说。“你看到了吗?”“不,我知道。我从小就在这里过夏天,我知道。”黑暗中,带着黄泥的老教堂没有灯光,墓地就在教堂旁边,十字架一排排立着,不知名的树在风中摇晃。被大灯照亮的破旧房屋都很大,上面住着人,下面住着牛马。气味不讨厌,但很农村。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边的十字路口等着。看到那两个高大的身影,我的心又痛了。那个小绯,我们叫他“楠”,在沙漠里总是骑在我丈夫荷西的肩膀上,那时他刚刚两岁多。现在,一个又高又瘦的长头发大眼睛的男孩静静地站在车头灯下。不要见面。“南——”我向他喊,他抿着嘴唇,一动也不动。冲向汽车的是那个胖胖的哥哥,名叫塞萨尔,脸上带着假笑。
我想下车,夏一米一直说要先回家。我说,孩子在哪里?让他们上车,还有强尼。说着,三人不走山路,斜着爬进树林,抄近路跑了。
推荐阅读
- 好的爱情是天堂,坏的爱情是地狱
- 90后结婚后,比婚前更孤独
- 子夜荐读 | 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 三毛流浪记主演 《三毛流浪记》的扮演者已长大 曾因头部受伤息影7年 至今单身
- 子夜荐读 | 纠结无用,不如让心思简单些
- 子夜荐读 |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 子夜荐读 | 有一种自律,叫熟不逾矩
- 子夜荐读 | 人到中年,要学会给自己看“病”
- 子夜荐读 | 人生如镜,镜透百态
- 武汉市漫画研究会新任掌门人蒋勇呼吁:“三毛式的传统漫画急需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