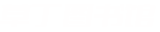“他喜欢一些有边缘感的词。他的词汇里有很多‘好像’,很多‘好像’,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这些话看似模棱两可,比较笼统,实则表达了孙甘露对空极其犀利的感情。他很少把自己放在安全地带或舒适的时间区域空,他徘徊在边缘,他在附近测试自己。”当毛健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察时,孙甘露望向远方,轻轻点了点头。
在一篇名为《慢》的短文中,孙甘露这样描述写作:“就个人而言,写作是内向、敏感、懒惰、尖锐、矛盾和渴望的。我把希望寄托在读者身上,但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一切并不取决于写作的质量,而是决定了作品的质量。最后,文笔简单明了。但这不是借口。写作是对位和复调的。但它不是抽象的。它的简洁性和复杂性具有感觉特征,它存在于神经末梢。”
在情感上,他更倾向于有沙漠经历的边缘作家,比如葡萄牙诗人费曼多·佩索阿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这两位写手相对自由,像主流写作中的焦点不对齐,或者像以前的射频调制不调整,这都伴随着当下声音的感觉。”
巧合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向京刚刚写完《论韩少功》,而正是韩少功将佩索阿的《安冉鲁》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译成了中国,引起了轰动。“孙先生特别喜欢翻译文学,韩先生也很重视翻译。韩先生不是专业翻译。作为一名作家,他选择并引进了一种文学传统来翻译外国作品。世界上有很多文学传统,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翻译就是为当时的文学创造一个充盈的文学传统。”向静说。

文章图片
作家孙甘露
对自己的语言不熟悉
在一次谈话中,孙甘露和罗刚谈到了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一个作家原本是外国人,他的工作是翻译他内心的声音。这个过程比外语更异质,它包含了一种生活。”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孙甘露把“用自己的语言做一个陌生人”作为一种理想状态。
罗刚称孙甘露的语言探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语言突破”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非常重要,它孕育了现代白话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但问题是,除了鲁迅这样的少数作家,大多数作家的写作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欧化刻板印象’或‘学生腔’。”
罗刚说,当时纠正“欧化刻板印象”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归传统的中国语言,即林语堂等人提出的“如何将白话文洗入文字”;另一种是回归到中国人爱听、爱听的生动活泼的“口头叙事”。“口头叙事”确实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中产生了杰作,但它逐渐与官方主流语言结合,变得僵化。“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安忆写的《萧》中的一个细节。小说描写“捞渣”是“仁义”之举,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但是,小说里有一个疯子,整天为县里出力。与普通人讲的故事相比,他写的‘捞渣子’的故事完全走样了。”
如果说“口头叙述”是“第一次语言突破”,罗刚认为第二次语言突破是“回到以孙甘露为代表的书面语言”。
“这种回报是从国外获取养分。孙甘露特别喜欢翻译文学,这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翻译文学已经成为现代汉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官方刻板的语言再次突破。甘阳编了一本书《80年代的文化自觉》,里面有些文章全是西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西学能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对于刚才的问题,昆德拉和佩索阿为什么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感觉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并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变成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推荐阅读
- 喜茶上新轻芒芒甘露,延伸自经典产品带来清爽体验
- 祖孙喝偏方凉茶后中毒了!医生:砷浓度超出正常值8倍
- 伯辣图 王勤伯疑似再度叫板孙杨:任何指责我不务正业的人都是反动派
- 婆婆逼我乱吃药,还说吃了就能生孙子,我该怎么办?
- 奶奶给2岁孙子喂毛豆致右肺堵塞!医生:3岁以下最好别喂这些……
- 孙红雷电视剧 《征服》后 孙红雷又一部打黑剧来袭 演员阵容选得有点意思
- 孙雅 孙雅智:为更多的人谋幸福 就是自己最幸福的事儿
- 三星集团控制了韩国吗 韩国三星集团会长16岁孙女曝光 天之骄女容貌超像徐睿知
- 罪夜无间 今日影视推荐:《罪夜无间》王泷正携甘露共同破案
- 婆婆去儿子家带孙子,两年后决定打道回府